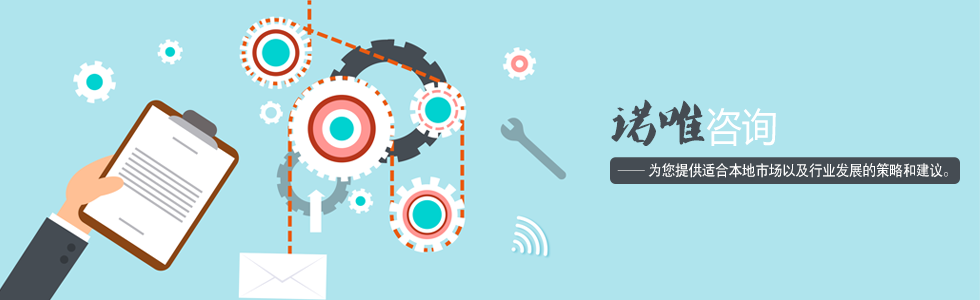深度访谈作为定性研究中的方法, 在目前的社会学领域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所谓深度访谈, 学界所指的主要就是半结构式的访谈 (semi-structured depth interview) , ( Hakim, 1987; Arksey & Knight , 1999; Wengraf, 2001)。汤姆·文格拉夫提出了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 第一: “它的问题是事先部分准备的(半结构的) , 要通过访谈员进行大量改进。但只是改进其中的大部分: 作为整体的访谈是你和你的被访者的共同产物( joint production)”; 它的第二个特征是“要深入事实内部”(Wengraf, 2001:3)。
关于第一个特征, 文格拉夫指出, 访谈员事先准备的访谈问题必须要具有开放性。在访谈中, 被访者对事先准备好的问题的回答和随之而来的问题都是研究者无法预知的, 因而, 访谈必须“以一种谨慎的和理论化的方式来加以改进”(Wengraf, 2001:5)。这一特征已经成为关于深度访谈的基本共识, 也是我们对访谈的基本主张之一。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 研究者不能试图去确定和提出每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具体问题, 甚至也不能够事先确定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在准备过程中,“半结构式的访谈应当只确定主要的问题和框架, 访谈员应能够改进随之而来的问题, 同时探究意义以及出现的兴趣领域。在事先确定主题和话题领域的情况下, 要渴望听取被访者的叙述。但访谈员也要注意改进问题, 以澄清或者扩展回答”(Arksey & Knight, 1999: 7) 。在此前提下, “尽管访谈员足以将谈话导引到感兴趣的题目上, 深度访谈还是会为被访者 提供足够的自由,他自己也可以来把握访谈”(Hakim, 1987:27)。
但是深度访谈最重要的目的还在于它的第二个特征, 即“深入事实的内部”。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个是何谓“深度”, 一个是如何能够深入事实内部? 关于“深度”, 文格拉夫提出了两点:
1.“深度”了解某事乃是要获得关于它的更多的细节知识。2.“深度”指的是了解表面上简单直接的事情在实际上是如何更为复杂的; 以及“表面事实”( surface appearances) 是如何极易误导人们对“深度事实”的认识的。(Wengraf, 2001:6)
文格拉夫强调了更为丰富的细节知识和事实之间的意义关联。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对深度访谈之“深度”的全面解析。联系到格尔茨所 强调的“深描”(格尔茨, 1999P1973) 就会发现, 文格拉夫并没有关注访谈员在深度访谈中所遭遇到的舒茨所谓的两个世界的问题(Schutz, 1976)。换句话说, 所谓“深度”的问题, 是与如何达到深度的问题密切相关的。而深度访谈的实质, 并不是仅由对待“深度事实”的态度所构成。如果对深度访谈的具体方法没有清晰的认识, 也很难达到访谈的目的。
格尔茨主张在面对复杂而又含混的文化结构时, 首先掌握它们, 然后加以转译。这种掌握是以被访者概念系统来完成的。研究者要进入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去, “必须以他们用来界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那些事的习惯语句来表达”( 格尔茨, 1999/1973: 18) ; 然后再将所得信息“转译”为社会研究的语言, 对此信息的意义给出解释。所谓深度的事实, 从意义的角度来说, 首先是要了解它对于被访者而言的意义, 然后才能够考虑研究者的意义情境。
对于深度访谈的态度直接由对待定性研究的态度决定。在访谈当中面对叙述者的时候,我们想获得什么?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意凯瑟林·哈克姆( Catherine Hakim)的观点, “定性研究关注于个体对他自己的态度、动机和行为的表述( accounts) ……, 定性研究的使用并不必然意味着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 也就是说, 并不意味着将所有的解释都归之于自我指向( self2directing) 的个体。但是人们关于情境的自我定义是所有社会过程的重要因素, 即使它没有提供完整的表述或者解释”(Hakim, 1987:26)。被访者在整个访谈过程中的所有表现都是研究者观察的对象, 并且是后者研究资料的来源。就意义角度而言, 这就又回到了韦伯在讨论社会行动时提出的观点: 社会行动是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的, 而这样的意义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 理解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是社会学的任务, 而且这样的理解必然与解释联系在一起。 访谈资料既然来自被访者的叙述, 那么这样的资料一定也是由被访者赋予了意义的(或者说, 这是经由被访者主观建构的叙述) 。因此, 一般说来, 对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可以大体等同于对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的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我们要理解并给出解释的则应是被访者赋予访谈资料(话语) 的意义。这其中包括被访者赋予这些资料的意义, 以及这些资料和被访者的行为对研究者而言的意义。此外, 我们还要关注访谈发生的场景, 因为被访者同样赋予其以某种意义; 并且该意义与被访者赋予自己叙述的意义是存在着某种联系或一致性的。
实现研究目的的前提在于对这种访谈资料的理解和解释。于此, 我们进一步认为, 深度访谈发生的过程同时也是被访者的社会行动的发生过程。所有被访者在访谈过程中的表现, 诸如动作、表情, 以及最重要的叙述行动也需要我们去观察、理解与解释(即在深度访谈这一获 取资料的过程中, 必须将资料的载体也纳入资料的范围之内) 。
但是这样的观察、理解与解释并不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访者的意义体系相混淆。我们应该在被访者的日常系统中完成对被访者的“投入的理解”和“同感的解释”(杨善华等, 2003) 。这也符合韦伯的原意, 也就是说, 对于行动的理解要将其放置在行动者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 但同时也要注意明确区分研究者与被访者, 即我们所理解的是行动者赋予行动的意义, 而不是我们研究者主观认为并强加于行动者的意义。舒茨将各个有限的意义域称为各意义世界, 进入社会科学的世界意味着放弃自然态度, 成为价值无涉的观察者(disinterested observer), 同时具备了与日常生活不同的意义关联体系。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既然社会科学与日常生活并非同一个世界,那观察如何可能? 即使论域限定在访谈之中, 问题也同样存在, 研究者如何首先获得对于日常生活中的行动者的理解? 舒茨认为:“当他(社会科学观察者)决定科学地观察这个生活世界时, 即意味着他不再把自身及自己的兴趣条件当作世界的中心, 而是以另一个零点取而代之, 以成为生活世界现象的取 向”( Schutz, 1962: 158) 。社会科学的观察者, 已经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参与者, 即使是在访谈类的观察中, 也非如此不可, 尽管访谈的特征是双方的互动。因为访谈一旦发生, 被观察者的日常生活也就停止。要完成从日常生活到社会科学世界的跃迁, 就必须将自己从实际的日常生活中抽身出来, “并将自己的目的动机限制在如实地描述与解释所观察到的社会世界中去”( Schutz, 1976: 17) 。所以, 如果研究者以社会科学观察者的“单一”身份来进行访谈, 就不能够从根本的意义上完成对被访者日常生活的了解。研究者首先要做的, 是与被访者共同建立一个“地方性文化”的日常对话情境。同时, 研究者还必须能够分清楚, 自身的世界——无论是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世界还是自己的常人世界不同于被访者的世界。研究者必须要防止以自身对于世界和事件 的意义性观点来取代被访者的观点。
因此,从意义的角度来看待“深度访谈”的实质,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它是对被访者在访谈时赋予自己的话语的意义以及被访者赋予访谈场景(包括被访者当时的衣着、神情、行动和居家环境) 的意义的探究。一旦研究者明确了这一点, 便可以一种积极能动的态度和立场去实现这样的探究; 而这种态度和立场的标志就是在访谈当时和现场就开始这样的认知。在这个意义上, 深度访谈既是搜集资料的过 程, 也是研究的过程。
那么, 我们如何能够在保持与被访者之间的疏离关系的基础上, 来获取足够“ 深度”的知识? 访谈又应当如何展开呢? 阿科瑟与奈特提出了与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相应的一种访谈方法, 称之为“渐进式聚焦法” ( progressive focusing) 。这种方法是从一般化的兴趣领域入手, 逐渐发现被访者的兴趣点, 然后再集中展开。因为在访谈中, 被访者会对他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更多的叙述和表达。在访谈中, 这种半结构式的、开放式的谈话目的是为了“从人们的话语中了解人们在情境中的问题领域, 并试着用他们自己的术语来了解事情”(Arksey&Knight, 1999:18)。文格拉夫也认为, 被访者一般的兴趣都在于自身生活史, 而这正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定性研究的一个现象, 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生活史转向。